投诉电话:0997-8662298
投诉邮箱:twzx@tarp.edu.cn
纪委信访举报
投诉邮箱:tlmzyjsxyjw@163.com
举报电话:0997-8662289

朔风是从塔克拉玛干的腹地里钻出来的,裹挟着沙砾与寒意,刮过阿拉尔的戈壁,便把天地刮得一片肃杀。这风不比江南的软,也不似北国的烈,却带着一股子戈壁独有的粗粝,打在人脸上,是生疼的,却又让人清醒得很。
天是灰扑扑的,像是蒙了一层洗不净的尘。雪是落了,却下得吝啬,薄薄一层,盖不住干裂的土地,反倒衬得那些褐色的土坷垃,越发显出几分倔强来。道旁的胡杨早落尽了叶子,光秃秃的枝桠伸向天空,像极了那些垦荒人瘦骨嶙峋的手,几十年前,便是这样的手,刨开戈壁的硬土,种下了第一株树苗。
日头是难得露脸的,便是露了,也没什么暖意,惨白的一团,悬在天上,看着倒像是病了。风依旧是刮着,卷起地上的雪沫子,打旋儿,撞到墙上,又散了。路上的人不多,都裹着厚实的棉衣,缩着脖子,步子迈得匆匆,嘴里哈出的白气,一冒出来,便被风吹散了,留不下一丝痕迹。
兵团人的屋子,却总是暖的。土炕烧得滚烫,炉上的水壶滋滋地响,腾起的水汽,糊住了窗玻璃,凝出一片片冰花。老人坐在炕沿,抽着旱烟,烟袋锅子在炕沿上磕了磕,便说起从前的事。说那年雪下得齐腰深,他们穿着单薄的军大衣,在雪地里刨坑种树,手冻裂了口子,流出血来,和雪融在一起,竟也不觉得疼。说这话时,老人的脸上没什么表情,只是眼角的皱纹,像是被风吹得更深了些。
孩子们是不怕冷的,在屋外的空地上追着跑,手里攥着雪球,扔出去,砸在同伴身上,便爆发出一阵笑。那笑声清亮,在这肃杀的冬日里,竟像是一道光。麻雀落在光秃秃的树枝上,歪着头看,被孩子们的笑声惊起,扑棱棱地飞远,又落在另一根枝桠上,叽叽喳喳地叫着,像是在抱怨这扰人清静的孩童。
暮色来得早,风也越发紧了。路灯亮起来,昏黄的光,在风里摇摇晃晃,照着地上薄薄的雪,也照着那些沉默的胡杨。这阿拉尔的冬,是冷的,是硬的,却又在这冷硬里,藏着一股子热气——那是垦荒人埋下的根,是一代代人,在戈壁上,生生不息的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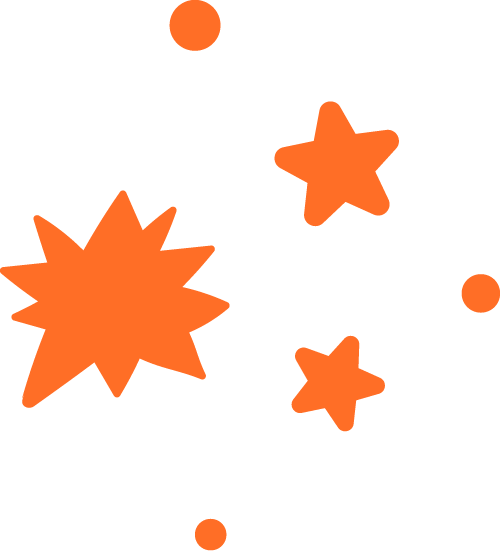
阿拉尔的风,总带着戈壁的苍劲,卷着塔河的水汽,掠过窗外的胡杨。今天,风里却凝着一丝遥远的寒凉——是八十四年前,南京城的雪,簌簌落在冰冷的城砖上,落在三十万同胞的骨血里。
我站在西北的暖阳下,指尖划过手机屏幕上的黑白影像。城墙倾颓,街道死寂,那些蜷缩的身影、绝望的眼眸,隔着千山万水,却像一根淬了冰的针,一下下刺得人心口发紧,疼得喘不过气。三千里外的南京,此刻该是素缟萦城,警报长鸣。而在阿拉尔,这片曾见证屯垦戍边、孕育过无数新生的土地,风掠过胡杨的枝桠,也似在低低呜咽,一声声,诉着那段不敢忘、不能忘的历史。
没有亲历过烽火,却能从史料的字缝里触摸到刺骨的痛。那些数字,从来不是冰冷的符号,是父亲护着孩子的最后一声嘶哑呼喊,是母亲抱着婴孩的绝望啼哭,是无数个家庭在炮火里的骤然破碎,碎得连一丝完整的念想都留不下。三十万,这沉甸甸的数字,刻在民族的脊梁上,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。它不是尘封的过往,是警钟,是烙印,是我们回望历史时,必须含泪铭记的伤痕。
阿拉尔的胡杨,扎进戈壁的根须就没打算退缩,活着便把绿意绽到极致,就算枯了,也挺着一副铁骨不肯弯折,哪怕倒在沙砾里,身躯也久久不腐,守着这片土地岁岁年年。这倔强的生命力,何尝不是民族精神的写照?从南京的废墟里挣扎着站起,从山河破碎中浴火重生,我们今日的和平,是先辈用血泪换来的;我们脚下的土地,无论是江南的烟雨秦淮,还是西北的大漠戈壁,都承载着同样滚烫的家国情怀。
警报声在脑海里回响,穿透时空的阻隔。雪落无声,历史有声。站在阿拉尔的土地上,我望向东方。那里,有一座城,以国之名,祭奠亡魂;那里,有一段史,以血为证,警示来者。
和平年代,无需我们披甲上阵,但我辈青年,当以史为鉴。铭记,不是为了延续仇恨,而是为了守护和平;缅怀,不是为了沉溺伤痛,而是为了砥砺前行。
风停了,阳光洒在胡杨的金叶上,熠熠生辉。愿以吾辈之青春,护佑盛世之中华;愿山河无恙,国泰民安。